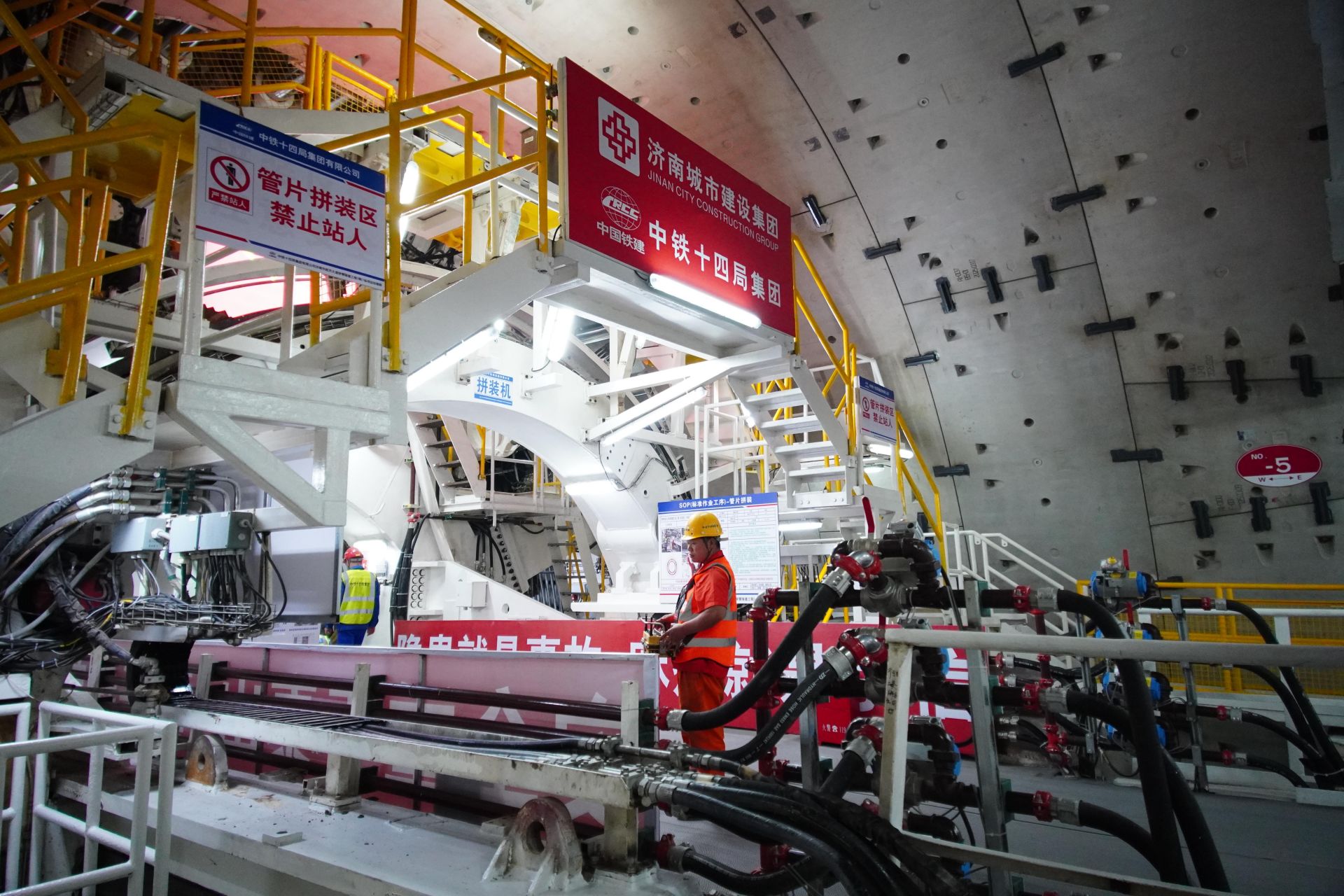天還沒透亮,漁港的早市已咕嘟咕嘟冒著熱氣。穿花布衫的漁家阿嬤支起油鍋生火,米糊裹著新鮮的海鰻魚塊,隨著沸騰的金浪在油鍋里翻涌,香味伴著海風鉆遍每條巷弄。騎摩托車的婦人在車后挎著竹籃,頭發上的露水還沾著早晨拜祭法令公的香灰——她們要趕在頭船歸港前,搶兩籃肥美的馬鮫魚賣個好價錢。
法令公廟前的石階被晨霧洇得發亮,賣香紙、水果的小攤列成方陣。老船工們蹲在廟門口卷煙卷。煙絲是附近村民種的,裹著曬干的海棠葉,抽一口能嗆出半輩子海腥味。“昨夜北斗沉得低,今日保準網不空。”王伯瞇眼瞅著供桌上油亮的閹雞——這是烏石港人給神明的至臻心意。
港口的鐵皮船“突突突”地吐著煙圈,甲板上堆著新漆的浮標,橙紅翠綠活像撒了把彩虹糖。后生仔們赤腳在船舷邊躥跳,將從媽祖求來的平安符系上桅桿頂端。銀灰色的海鷗悠然掠過粼粼波光,尖喙一伸叼走了半塊蝦餅。拴纜繩的老李手攥粗麻繩晃了晃,古銅色臉龐的皺褶里漾出笑紋,操著方言笑罵:“這扁毛畜生膽子夠大哦,下次再讓我瞅見,必捉來拔毛,夠配三斤老酒咧!”遠處漁船正巧鳴起歸港的長笛,驚得另一群海鷗撲棱著翅膀掠過桅桿,海天之間蕩起細碎的銀鱗。
日頭攀上桅尖時,整個海灣成了一口沸騰的大鍋。漁家女們坐在陰涼處織補漁網,尼龍線在指尖翻飛如銀梭,家長里短比網眼還密實:“昨天老張家媳婦剖了一條肚里藏玉的黃花魚!”“要我說啊,媽祖愛看雷劇,該請劇團來唱三天雷歌,勞動節就鬧得掀到了海龍王殿頂!”路過的小花邊說邊興奮得晃著辮梢:“‘五一’有安排啦!烏石雷歌學會要舉辦聯歡會,有雷歌對唱、詩歌朗誦、流行歌、三句半呢!”
隨著白晝推移,潮水悠悠退去。沙灘仿若一本翻開的厚重史書,緩緩露出古老而滄桑的“齒牙”。貝殼緊緊將“耳朵”貼在礁石上,似在探尋歲月流逝的痕跡。灘涂上冒出星星點點的彩傘:城里來的畫家支起畫架,筆尖蘸著海風涂抹勾勒,卻總畫不圓拾貝孩子笑裂的嘴角;穿膠皮褲的趕海人彎腰如雁陣,蟶耙劃過沙地的痕跡,似是給大海的情書添上歪斜的注腳。
夜幕悄然而至,墨色如濃稠的汁液,將烏石港緩緩包裹。遠處的燈塔,似一位堅毅的守望者,散發著柔和而明亮的光,穿透夜幕,將最后一縷余暉灑向如鏡的海面,那片云彩也在這光輝里漸漸隱去蹤跡。
剎那間,烏石港像是被施了神秘的魔法——停泊在港灣的漁船,桅桿上的盞盞漁火在夜幕下閃爍,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仿佛繁星墜落,繪就一幅如夢似幻的璀璨畫卷。漁火搖曳,似在與初夏的海風低語,又似是應和著這方土地獨有的詩意。
港灣邊,錯落有致的漁家燈火次第亮起。灶間彌漫著誘人的酒香,那是漁家自釀的佳釀,散發著醇厚的氣息。隨著鍋鏟的翻炒,蒜末爆鍋的“滋啦”聲接連響起,像是奏響一曲歡快的夜曲。鐵鍋里,油燜大蝦紅亮誘人,在熱油中歡快蹦跳,釋放出陣陣鮮香。
街邊的小店也亮起溫暖燈光,蜜雪冰城前排起長隊,三五成群的年輕人坐在海邊,吃著燒烤,海風輕拂,滿是愜意與自在。
不知從哪戶人家的窗欞間,飄出一句雷歌:“五月漁郎心似火”。然而,后三句還未聽清,便被悠悠濤聲裹挾而去,只留下滿港的歡聲笑語在夜色里肆意流淌,訴說著烏石港獨有的溫柔與熱鬧。
法令公廟前的空地,石板桌椅坐滿了人。后生們摔跤比腕力,古銅色脊背淌著油汗,在月光下泛著鯖魚油般的光澤;阿公們叼著煙桿對弈,棋子是海里撿的虎斑貝和鸚鵡螺,輸一局便罰唱段咸水歌或雷州歌;最頑皮的娃兒們舉著熒光棒你追我趕,將漁港的夜攪成流動的星河。
潮聲漸酣時,守夜的老船頭摸出嗩吶,一曲《漁家喜訊》雷州方言歌乘著海風盤旋,驚醒了船塢里打盹的斑海豹。樂聲纏著月光,繞著媽祖廟的飛檐而轉,輕輕地落進每扇亮著燈光的窗戶。
在剖魚的案板上,新腌的鰻魚醬正裹著初夏的陽光發酵;在算賬的算盤里,頭船馬鮫魚的斤兩蹦跳著撲進賬本;在孕婦輕撫的腹中,未出世的漁家娃聽見潮聲里的雷歌美調,滾動著欲奔出看熱鬧……
這些被海風釀了千年的故事,終將隨著初夏的漲潮日,在新的漁汛里重新蘇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