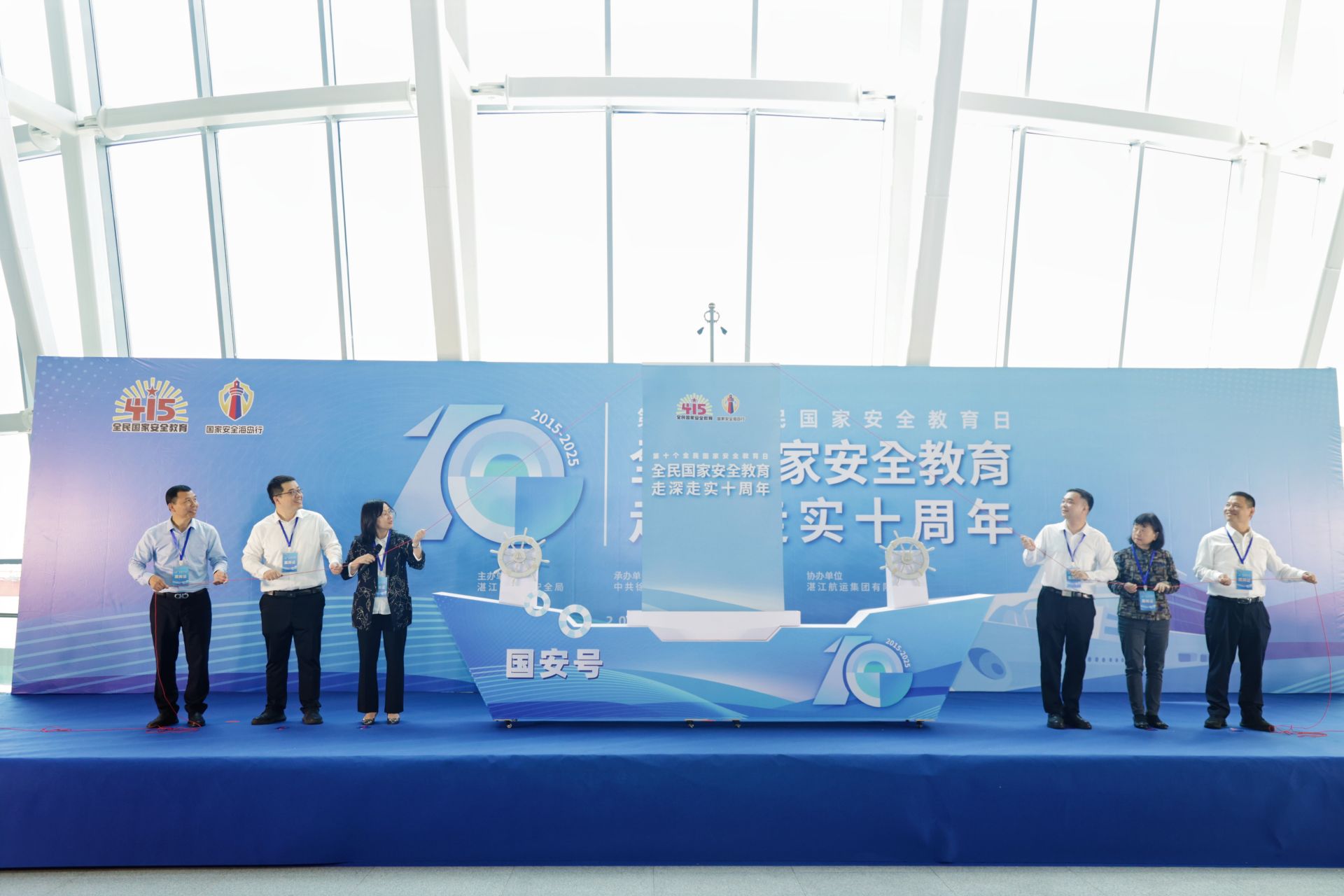作為威爾第著名的“通俗三部曲”之一,歌劇《游吟詩人》自19世紀首演以來廣受歡迎,近日,國家大劇院制作《游吟詩人》第四輪登上舞臺,再次展現了經典常演不衰的巨大魅力。

《游吟詩人》劇照。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 方非攝
從故事到音樂,《游吟詩人》張力飽滿:劇情脈絡上,跨越兩代人的復仇計劃、同胞兄弟的生死較量環環相扣,“狗血”但精彩,仇恨與寬恕、自由與宿命等話題永不過時;音樂表現上,威爾第在作品中運用了精妙的技巧和構思,女高音、男高音、女中音、男中音、男低音5個聲部每個都要出彩,是一部不折不扣的“唱功戲”。
本輪復排,國家大劇院版《游吟詩人》集結了阿馬迪·拉加、伊沃娜·索博特卡、馬爾科·卡里亞、克里斯蒂娜·梅里斯、阿德利亞諾·格拉米尼等歌唱家領銜的國際組,以及王沖、周曉琳、周正中、牛莎莎、關致京等歌唱家領銜的中國組兩組陣容。在音樂內容的呈現上,《游吟詩人》的這次演出可謂圓滿,游吟詩人曼里科的“柴堆上火焰熊熊”、女主角萊奧諾拉的“愛情乘著玫瑰的翅膀”、吉普賽婦人阿蘇茜娜的“火焰在燃燒”等經典唱段被完成得相當出色,萊奧諾拉的飾演者之一、波蘭女高音伊沃娜·索博特卡尤其亮眼,她歌喉華麗,一登臺便立住了角色空靈美好、幽思縈繞的特質。索博特卡的弱音如天鵝絨柔美,高音穩健而有穿透力,終幕瀕死時,她的顫音與逐漸消散的氣息情真意切,弱而不斷,把萊奧諾拉為愛獻身的悲劇色彩推向了頂點。

《游吟詩人》劇照。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 方非攝
此外,在指揮家皮耶羅·里佐的調動下,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的演奏為整部作品鋪墊了流暢遞進的底色,忠實還原了威爾第總譜上的種種構想。流動于舞臺各處、靈活扮演群眾角色的國家大劇院合唱團同樣表現到位,在著名的“鐵砧大合唱”中,恢弘而不乏層次的演唱酣暢盡興。但與音樂完成度上收獲的好評相比,《游吟詩人》的舞臺呈現顯然更有爭議:這個首演于2014年的版本由導演烏戈·德·安納操刀,大幕升起,他在舞臺上鋪開倒塌懸置的立柱和雕像,在混亂的荒誕感中牽引出令人唏噓的悲劇故事。隨后,導演綜合運用舞臺設計和多媒體技術,引入火焰、月球、星云等視覺形象。他的意圖不難被察覺,這些超越現實的元素意在搭建一個抽離的、模糊了時空界限的敘事空間,進而讓《游吟詩人》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喚起觀眾的思考和共鳴。

《游吟詩人》劇照。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 方非攝
但有點可惜的是,從實際的觀演體驗來看,導演的設想好像未能穩妥著陸。《游吟詩人》的故事發生在15世紀的西班牙,舞臺上演員們的服裝都有明顯的時代特征,但過于“耀眼”的聲光電手段,仿佛直接把這部以中世紀為背景的歌劇套進了《星球大戰》,在守正與創新的天平上,這一版《游吟詩人》有些躊躇不定,于是呈現出一種糅雜的凌亂——當科幻感十足的月球與星云出現時,除了以割裂的觀感分走觀眾的注意力,似乎并未起到激起深思的效果。誠然,在如今的舞臺上,對經典作品進行當代包裝是相當常見的手法,但“新”的尺度和意義,是需要創作者慎之又慎的關鍵所在,僅僅為新而新、為刺激而刺激,作品本身的光芒反而會被不必要地沖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