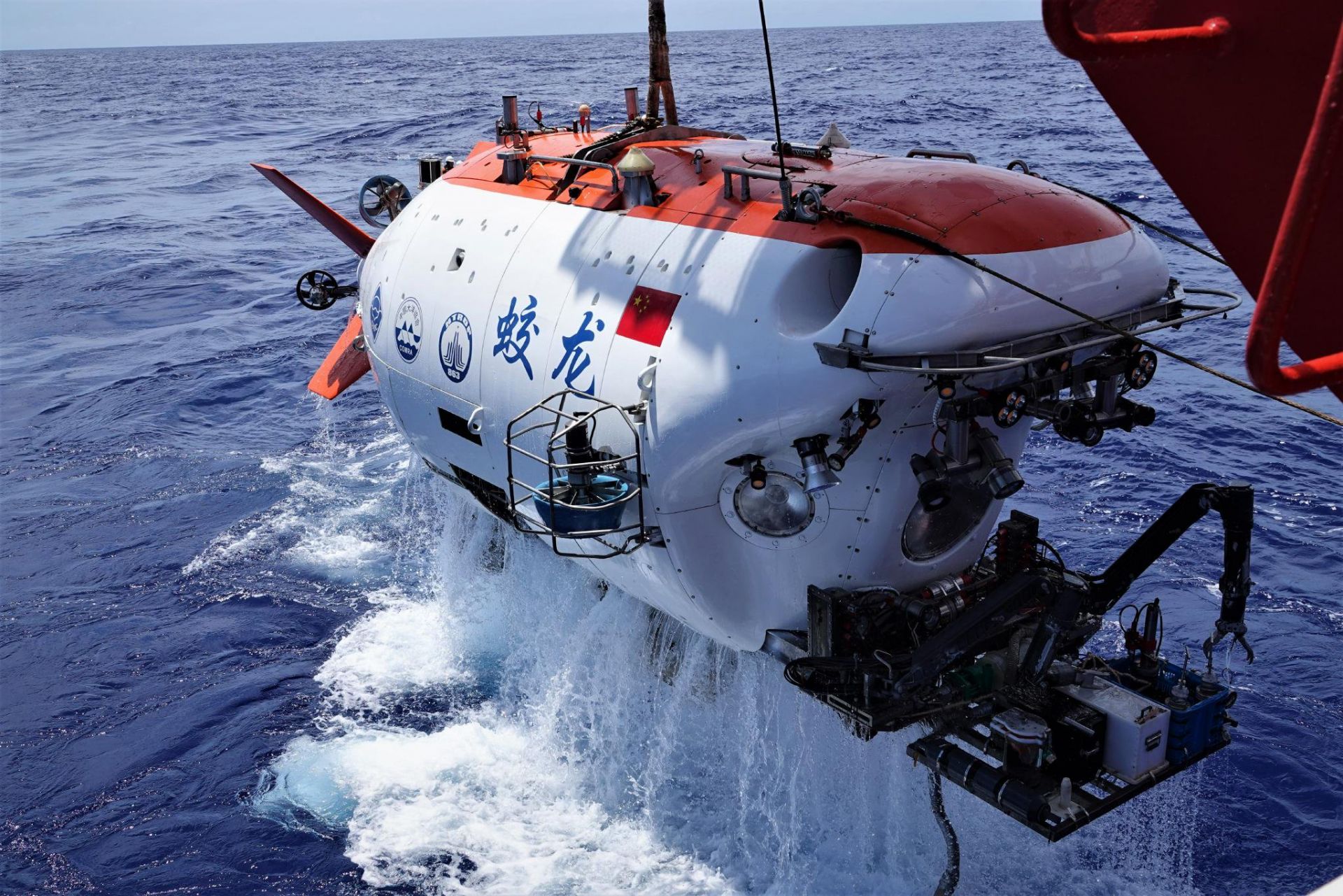在浮山嶺的東麓下面,有一條村子的名稱不一般:古城。它,隸屬于茂名市電白區霞洞鎮下中行政村。
如今,進入這個古城村,是見不到任何古城影子的。它跟周圍的普通的村子沒有多少差別。它從前曾經是一座城呢,這是考古專家說的。二十年前,鎮里文化部門的人領著省市縣專家考古,在村子里挖出了城墻的基礎,挖出了隋磚唐瓦。挖了出來,又埋了回去,等候再一次更高級別的保護性發掘。
隋磚唐瓦被埋了回去,但塵封不住一個美麗的傳說。
公元五三六年,出生于丁村的俚人女兒冼氏與高涼太守馮寶成婚,從此被稱為冼夫人。這一對新人有新家,在風光秀美的地方,既不是馮寶祖籍老家新會,不是馮寶老爸執政的羅州城,不是馮寶執政的高涼城,而是離丁村七十里的浮山之陽,瑯水之陽,如今叫霞洞鎮。新家初時不太大,只有如今的霞洞中學那么大,正是霞洞中學那塊地。興建這個新家,馮寶的老爸全額投資,只是設計征求了一對新人的意見,融進了新人所需要的諸多元素。馮寶的老爸是誰呢,他是羅州刺史馮融,經營多年,政令不便,為改變局面,找個俚女為媳。為兒子媳婦新家著想,他將積攢的老本都花上了,建得堂堂皇皇,叫馮家村。
不久,冼夫人也花本錢為自己的特別嫁妝一一冼家軍,安一個家在浮山腳下。不是因為她是刺史的兒媳,更不是因為她是太守的妻子,只因為她已是俚酋。俚酋,就是嶺南百越族俚人一個大部落的頭人,稱作都老,有權有勢,所以嫁妝有兵有將,兵將有千人左右。
這支冼家軍,被安頓在馮家村東面不足十里遠的浮山腳下,如今那里叫新營村。昔日叫新營,住所是干欄式房屋,如今稱之為木棚。那是冼夫人依俚人習俗而作的干欄,好大的一片,住下了她的千軍萬馬。她親自帶領將士們上山伐竹伐木,將水桶粗的大樹鋸成木板,然后搭起干欄,架成床鋪,干得又快又好,只有半個月就完成的干欄,對于漢人,很是新鮮。附近的漢人聞訊前往參觀,都豎起拇指稱贊呢。干欄不是低矮的木棚,而是高高的吊腳樓,床鋪離地五尺,防濕,防蛇,防獸,且留著大樹遮陰,空氣清新宜人,住著挺不錯。
過了幾年,冼夫人在馮家村住慣了瓦房,將士們住舊了新營的干欄。她看到附近漢人都住瓦房,遮風擋雨防寒要比干欄強,慢慢地萌生了將新營干欄改造為瓦房的念頭。征求丈夫的意見,得到的回答是:“不謀而合!”征求將士們的意見,更是個個全力支持。
要建多少間兵營瓦房呢?冼夫人與將士們商量,結果:建瓦房二百二十間,每間住五人,剩下的用于辦公或作他用。
說干就干。將士們按照冼夫人的規劃和設計,破土動工就忙個不停。這支冼家軍,聽到都老銅鼓的指揮,戰時奮不顧身,農時也毫不惜力。此時,在建筑工地上揮汗大干一場,為自己造新營房。挖土基時,有人挖出了又白又嫩的大石頭,準備用它來砌墻腳。未待砌墻腳,先用它支撐瓦鍋煮飯吃。在熊熊的柴火中,瓦鍋下面的白石碎裂了。說時遲,那時快,瓦鍋往下掉,爛了,瓦鍋里的水自由了,一個勁地往下流。流到木炭,激起陣陣濃煙和炭末。流到剛碎裂的白石上,奇跡發生了:白石頓時在“仙氣”中變成乳白色液體,熾熱灼人,粘性很好,冷卻凝固后,特別是跟沙子結合后,堅固如磐。原來,那些又白又嫩的大石頭是石灰巖,俗稱石灰石,燒過后變成石灰。石灰混水變成了石灰漿或石灰水。石灰漿與沙子配合,是一種很好的建材。冼夫人知道這些事后,命人收集挖出來的石灰石,制成石灰,專門用于自建瓦房。如今,那個地方不遠處成為石灰巖開采場的遺址,成了石灰窯的遺址。采石處剩下深深的池塘,養出的魚重達三四十斤。
建瓦房,所用的建材比干欄復雜得多,磚瓦是主體。一下子要購足建兵營瓦房的磚和瓦,當時辦不到。冼夫人迎難而上,自制磚瓦。冼夫人還在附近辦了磚瓦窯。制造磚瓦,工藝與制瓷有點相仿。首先要找到好的黏土,采出來練一番,練至十分軟熟。在練黏土時候,用人的腳板去踩踏,用牛去踩踏,反復進行。冼夫人卻別出心裁,用戰馬去踏,數百匹戰馬輪流上陣,黏土踏得又快又熟,保證質量過得硬。練好黏土后,經過將士們的雙手,經過制磚制瓦的模子,做成磚坯子和瓦坯子,晾曬至干,裝進窯里,用柴燒窯,燒上兩天兩夜,窯頂由黑煙變為白煙,再變成彩色的火焰。燒制磚瓦,最講究火候,不到火候生產出來的是“夾生飯”,受不了多少壓力,上不了墻頭;火候過度的或燒成粘連的“連體”或燒成歪眼斜鼻的“殘廢”。所以,冼夫人格外小心,專門聘請漢人老師傅前來“看火”,報酬比別處多一倍,還有好魚好肉招待。好心有好報,“看火”師傅打起十二分精神,使出真本事來,寸步不離地、專心致志地看火,面頰被窯火烘得通紅,跟燒熟的磚瓦同色。冼夫人時不時到來慰問“看火”師傅,打賞綠豆糖水。就這樣,冼夫人“兵工廠”造出來的磚瓦響當當,遠勝于到遠地買到的。如今,那燒磚瓦的地方成了一個村子,村名叫瓦窯。
為了瓦房的建材,冼夫人組織隊伍上山采石頭,伐樹木。附近的浮山嶺坡,有的是石頭,當時是采之不盡,用之不竭。但是.冼夫人下令,先采容易采的,先采當用的,一般都要整個采回來,采回之后應打破的才打破。如果要在山上打破的,要經過冼夫人批準。這一規定確英明,為浮山保留了許多風景石。例如:浮山的一片大石,名叫“單船起雙帆”,傳說是風水石,它的附近是風水寶地,保持好了,就能出將出相,富不可言。又有一處,巨石像人,比電白與陽江界山的望夫石漂亮得多,石所處的地方美如仙境。對這兩處大石頭,冼夫人都給予了應有的保護。如今,那塊“單船起雙帆”大石依然在,名字依舊不變;那塊像人的巨石,依然屹立在高高的山崗上,被人稱為“婆石”,它的形象望有點像冼夫人,英姿颯爽。冼夫人采石又護石,采木也護木。她下令給將士,進山伐木要留種,每隔一定距離將特大的樹木留下作“種樹”。留下的“種樹”,后來叫“木影”,直到它自然死亡為止。它結出的果,一年一年地繁殖成千千萬萬的新生命。怪不得,前些在沙瑯江車塘灣打撈起來的“烏木”,樹體大得驚人。
建材就位,萬事俱備。擇個吉日,冼夫人為新建兵營房奠基,一千將士和馮家村的人都到場。工地上,彩旗飄揚,鞭炮震響,人們喜氣洋洋。是大喜事一樁,世世代代住干欄的冼家軍就要住上大瓦房了,怎么能不高興呢。更為值得高興的是,這即將拔地而起的大面積瓦房,選址實在太好了:就在新營干欄側畔,背枕浮山,面臨瑯江,中間一馬平川,山清水秀,鳥語花香,有水道、驛道相連,交通方便,而且具有易守難攻的軍事價值。部下都贊冼夫人:“夫人獨具慧眼,選對了營址,在這里住過的人都要感激你。”冼夫人和藹地說:“為將士們辦好事,我心也快樂。這里的確不錯,有地理優勢,依山傍水,地勢開闊平坦,四通八達,大有可為,將來還可以發展為城邑。”
還真讓冼夫人說對了,那個地方終將發展為一座城。那座城,名叫良德城。
梁陳隋三代,冼夫人在浮山下打造的兵營大瓦房,住的都是將士,插的是冼字或馮字旗。到了唐代,冼夫人之孫馮盎成了馮家村的主人,也成了大瓦房兵營的主人。他以二十州之地降唐后,被封為吳國公(后改越國公、耿國公),授上柱國、南州總管,唐太宗給他增加一個縣,良德縣,隸屬于高州。有縣須有城,此城須自行解決。馮盎把良德縣城放到哪里呢?經過一番思考后,他作出了決定:實行軍政合駐,將浮山下兵營瓦房騰一半出來作縣衙;被“騰”的將士,與未“騰”的將士,輪流住回干欄式兵營。
馮盎在政治、軍事、經濟上都具有超一流水準,馮家村建成了嶺南第一村。馮盎的兒子馮智戴,當了唐太宗的侍衛將軍,一次智戴在李淵的宴會上吟唱占詩,博得滿堂喝彩,李淵贊嘆不已。智戴的兒子馮子游,載著滿船的金子到涼城探父兼游,吸引著千萬人的眼球。不久,子游把武則天宰相、大文豪許敬宗的女兒(史稱許夫人)取回馮家村,把喜慶的鞭炮燃放到良德城。在馮子游手中,良德城得到了擴建和裝潢。
馮子游死后,馮家村和浮山下的良德城不久被毀。
良德城一去不復返,附近的人仍稱這里為古城,知情的人稱之為“苦城”。